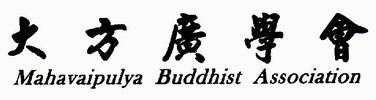十二緣起論(二)
◎楊崑生
十二緣起論為「佛學導論」的一章,以其自成章節,故引錄之。前期藉三世雙重因果之說法,引述十二有支的別相;進而就三世雙重因果說法的困境,闡述二世一重因果的意義。本期繼續以二世一重因果的不究竟,深入探討釋迦牟尼佛證悟實相境界的真實意義。 ─ 編者
(續前期)
前期談十二緣起,涵蓋了兩種說法:第一種是一般的說法,就是把十二因緣劃分成三個階段 ─ 過去生,現在生和未來生的「三世」。三世裡從過去因到現在果,然後從現在因到未來果,構成了雙重的因果關係,所以叫作「三世兩重因果」。第二種是藏傳佛教的說法,把無明從死亡的剎那來說,也就是指我們在死亡的過程中間,有一段黑暗時期 ─ 是真正的黑暗,物理上的黑暗 ─ 這個黑暗時期,即是一種無明。從這樣的無明開始,就進入中陰的階段,所以在這個說法裡,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,乃至於觸、受、愛、取,全部表現在中陰身的階段裡,「取」和「有」兩支就相當於入胎和住胎了。剩下的兩支,「生」就是真正的生出來,以至於今生的「老死」。這種說法是從過去生的死亡剎那算起,到這一生的老死,只講一重因果。
這兩種說法都屬於一種較淺觀的層次,仍舊沒有離開時間的架構。
深觀的緣起說法
這深觀的十二緣起,不需要追溯到二世、前世,或者是更前世,它只是把人生痛苦的現象,用十二緣起的方式把它展現出來。也就是說,生命從無常的觀點來看,一切的受都是苦,沒有所謂的「樂受」在其中,當然,這個苦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定義,也就是「一切皆苦」的苦,實際上,它真正的意義,並不是一種感受性的苦,而是一種本質性的苦。只有在本質性的苦上,我們才可以瞭解人生的一切都是苦的。在這深觀的緣起說法,主要彰顯的是,我們現在之所以會產生「愛」、「取」這種不應該的執著,其根源即在於有一種「我執」。但是,「我執」的根源又是什麼呢?在佛家的語言來講,「我執」是一種「能所」的分別,也就是一種「主客」的分別。換言之,「我執」是因為「能所」產生對立以後,才有「我」的概念,或者說,因潛在的意識存在,這個「我執」要追究到「能所」才能開始有所瞭解。然而,這個「能所」平常是在一種很曚昧的狀態裡頭,往往會忽略掉這個「能所」,好像有點「忘我」,一下子之間,不太覺得外在的世間,跟我們有什麼差別,可是,在一「觸」之下,會使得「能所」的關係突然醒覺;也就是說,在未觸之前,雖然是一種曚昧的狀態,不太有很明顯的主客意識 (雖然它是潛在的) ,但是透過觸以後,這個主客的意議就醒覺出來了。這個主客的意識一醒覺,就開始產生很自然的「愛」、「取」、「有」和下面這一套:::於是一步一步地,會發現有很多的「我執」在前面,輾轉地緣起了這些苦果。如果這樣子回頭去看,就可以把這個十二緣起,由老死、生、有::到無明,從反方向找出「苦」的中心所在。
老死諦
老死可以看做是對無常與苦的總結,為什麼呢?因為老死所詮釋的就是一個很明顯的無常,而無常又是苦的中心含義,所以老死無非就是講我們當前所受的一切苦的總稱。從另一個角度看,老死並不要等到二十年或三十年後,我們分分秒秒都在老死中。所以佛說人命在呼吸間,不是說我們可以再活個幾十年然後去死,而是說我們分分秒秒地在死。是什這個老死或無常的現象,為什麼會存在呢?它的依據麼?
無常的開始
一切的現像,我們能夠談它的無常,它必定要有一個開始,而這個開始的現像會消失掉,然後我們稱之為無常。由此可見,老死的根據,就是有一個東西會現起,會生出來,因此老死的根據在『生』。也就是說,從老死裡面我們體會到會有無常的苦果,是因為我們曾有一個生命的現起。不僅是這一期輪迴的生命,我們現前當下的生命在剎那剎那地現起中。如果我這個生命在下一個剎那不再現起,對我來講,老死或無常都沒有意義。而正是有剎那剎那的生生,於是有一再一再的無常。
剎那的現起
老死若這樣地反省,它的根據在生。為什麼會有生呢?為什麼我能在時間之流裡,剎那剎那地現起呢?其根據就是先要有一個很現實的存在 ─ 一個「存有」。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現實的存在或至少是一套存在的規範,我也好,外境也好,都無從現起,因為根本什麼都沒有嘛!所以這個成為生的現起,必須要有一個存有的依據,要有一套現起的規範。
存有的最後依據,當然是這整個一般性的存有,但自這一般性的存有中,如何表現出我們個人獨特的生命,這或者是一套獨特的存有,或是一套獨特的現起規範。那是什麼呢?就是前表讀過的五蘊 ─ 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我們存有的基本形式便是一個「五蘊的存有」。而我們前面也說過,這個五蘊的存在,不是一個只有主體性自我的五蘊,這個五蘊是涵蓋著客觀世界的五蘊,是主客在一體的五蘊。在這樣一個「大存在」裡面,心怎麼去想,怎麼去受,怎麼去識,色怎麼定位,都有它的分際和限制在裡面。也就是說,這樣一套東西,有這樣一套運作和現起的規範,我們才有這樣相續現起的生命,才有不斷的生生。
老死:無常與苦
<
生: 無常的開始
<
有: 存在及其現起之規範
<
取: 五取蘊的執著
<
愛: 我執的凸顯
深 <
觀 受: 主客的凸顯
的 <
緣 觸: 主客的覺醒
起 < 六入:配備的齊全
<
名色:能所的對立
<
識: 差別的虛幻
<
行: 差別相的造作
<
無明:苦的根源
五取蘊的執著
然而這五蘊的規範,不是哪一個超越的主宰幫我們訂下來的。從五蘊的內容,可以瞭解到,它是透過我們的「識蘊」裡分別識的架構系統,然後再透過「行蘊」裡面的行的造作,才把五蘊這樣子展佈開來;這個識之所以要這樣分別,或行之所以要這樣造作,其背後就隱藏一個我們的執著。不是誰要我們去造作、去分別,而是我們自己要這樣去造作、去分別,所以我們的五蘊又叫做五取蘊。換句話說,這個五蘊,並不是個客觀的五蘊,它不是個「你理它不理它,它都會這麼存在」的五蘊。不,它是在深層意識的執著下這麼選擇,規定而成就的五蘊。所以,這個五蘊是「取」而來的五蘊,是依照我們執著地取,而成執著的存在。
所以「生」所根據的這種「存有」不是個客觀的存在,而是透過「取」,而形成的五蘊的存在。這個取,是一個錯誤的取;是一種帶著我見 ─ 法我見與人我見 ─ 的取。這種不斷地、錯誤地執取,它的根源一定要有一個動機 ─ 我怎麼會一直去犯這個錯誤?而又有什麼力量,推動著我繼續這樣地去取?這個根源推究起來,必在於一種強烈的欲望,也就是所謂的愛。欲生一方面會矇蔽我們的理性,而同時又能發出很大的作用力。
我執的凸顯
愛是一種希求,一種渴欲。它的本質還是貪。在世俗的看法、都認為欲望或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。有愛有恨,甚至敢愛敢恨,似乎唯其如此,人生才有趣味和意義。佛學看愛,這件事誠然沒有這麼高的價值,但也同意,是愛規定了我們的方向,不只是所謂人生的方向,而是整個生命的現起。愛除了表現成對外境粗顯的愛惡外,更深、更強而也更不易感覺的是那種對存有和存有的延續之愛。細看愛的狀態,常是很繃緊的,深切期待的,甚至是強迫的。愛越強烈,則緊張的程度也越高。為什麼會如此呢?因為愛的結構裡必然地要充分肯定一個能愛的自我和所愛的外境。對兩者愈認真,對愛的情緒也愈強烈。所以就這一重意義而言,所謂愛不過就是我執,包括人我執和法我執的高度凸顯。在這種愛的籠罩下所現起的取,當然也就成為一個錯誤的執取。
這樣一種愛的狀態是如何起來的呢?也就是說我執會凸顯或放大,它的基礎和條件在那裡?執著的根據必須要先有主觀和課觀的對立,若無明顯的主觀,執著便無從談起。而凸顯這一主觀意識的便是使意識產生內容的「愛」。
主客的凸顯
如果主客之間,不產生如此尖銳化的「希求」對立,則沒有那麼強烈的「取的行動」出來。而這種「愛」的狀,把這個深層的我,突然地勾起來了。所以它的根源在於「受」,而「受」的含意就是把主客之間的對立,極度地明顯化。
本來我見是潛藏的,現在我見透過刺激凸顯了;本來一個我,很小看不見,忽然間,在這一剎那,這個我變得這麼大,這是什麼原因呢?是「受」的凸顯作用。因為我太苦了,太樂了,這個大苦與大樂,把深藏的我,凸顯成一個很大的我。這個受,為什麼能把我見,這樣子凸顯出來呢?它的依據又在什麼地方呢?這個還要有一個前題,就是主客之間,是受到一個外來刺激,所以在心裡的過程上面,這樣一個刺激,在凸顯我見的前面,要有一個接觸。這種內外的接觸,或主客的接觸,就是我們的六根去攝納外面六境的接觸,亦即是根境之間的接觸。
主客的覺醒
態,我們通常把它形容成一種很緊張的狀態 │ 整個心都繃在那個地方。這樣一個「愛」的狀態,是如何起來的呢?一定先要有一個刺激,一個感受。假如坐在那邊安安靜靜地,外界不給它刺激,不會有很強烈的愛要起來;忽然間給了他一個刺激,主客立即對立,這個刺激就是「受」。要有一個刺激之後,才會產生一個很強烈的渴望出來;而渴望的強烈擴張,在於我們把我見提昇到表面層次來,使得主客之間,產生一個緊繃繃的局面,變成二個截然的對立體,好像敵人相見,分外眼紅。所以其根源,是把我見提昇得很強烈,可是我見是怎麼樣子被提昇得這麼地強烈呢?因為受到一個外界的刺激
六根去接觸六境的「觸」,一般的解釋是「接觸」;而真正做為「受」的依據的「觸」,卻有更深的含義。原來,我們主觀的根與外面的世界 ─ 主觀與客觀 ─ 從佛的證境上來講,是一體的,不可分的;亦即是一個覺悟的狀態,本來就沒有所謂主觀與客觀。這種沒有主觀與客觀的狀態,並不因為我們人的執著而有所改變,換句話說,我們可以去誤解這個世界,但是世界並不因為我們的誤解而產生扭曲,世界還是那個樣子,實相還是實相的樣子。儘管我們覺得有能、有所,有主、有客,有人、有我,世界並不因為我們這樣分裂而分裂。要讓主觀的六根與客觀的外境,真正地現出執著上的分別的時候,就是「觸」的作用 。
這種主客覺醒的「觸」的含義很重要,再試著以具體的「身觸」來解說。我們都有以身體去碰桌子的經驗,如果沒有碰觸的話,當然毫無感覺;但是心不在焉地,或專注在做些別的事情,身體碰到任何一樣東西,可以說是毫無知覺。這裡面的受,就是一個中性的受,甚至於無感覺有這個受,也就是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發生。但是一留心受碰的時候,就知道有觸,亦即是說,當一留心,有觸的時候,主客立分,乍然覺醒。這個觸的本身,就是使得在本來沒有主客之分的情況下,忽然之間,讓主客分別的念頭現起。
受所以會表現得那麼強烈,把自我與外界放大,其基礎即在於觸的覺醒;這個觸,產生主客之間一種很明顯的覺醒。忽然間覺得碰到了,如果完全無心的話,手碰上去,也不會覺得手是自己的手,或桌子是外界的桌子;可是開始感覺到有一種感受的時候,實際上已隱涵主客已分,然後才有所感受。所以,這個觸是很微細的,它使得本來沒有主客之分的地方,「碰」地一觸,即刻現起一個主客之分,然後「受」才感受這個東西。透過這個基礎,才有樂受、苦受,才能去更明顯地放大自我,然後才根據這個放大的自我,產生一個強烈地、很緊張的渴望出來。
「觸」在還沒有觸之前,是一種矇昧的狀態,不太分別得出主和客,透過觸,才產生主客的覺醒。但是,為什麼會觸呢?是依據什麼,才有觸的條件呢?無庸諱言,能夠使觸產生一種覺醒作用的前題,一定要有一套基本設施的提供。何謂設施呢?設施就是「既成裝備」,能夠給觸一個機會,產生一個「自我覺醒」,或是「我見覺醒」的設備。有了這麼一個基本設施,觸才可一觸即發,這個基本設施是什麼東西呢?就是我們的內六入和外六入。
配備的齊全
內六入 (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) 與外六入(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) 當初成為基本配備時,並不知何者為因,只知往前面看;反過來說,「觸」能一觸即發,使得這個我覺醒出來,是因為已經有了內六入和外六入的基本配備在那裡,否則無從發起。譬如說,我們已經長好了一個耳朵,長好了一個眼睛,長好了一個身體;而外界又是長好了這麼樣的一個世界,以至於我們有了可以一觸即發的可能性出來。所以觸的基礎,在於有了這麼一個內六入和外六入的基本設施。
雖然我們的設施有內六入和外六入,但是從實相的觀點來看,這內、外並不是相分的,內、外是互相緣起的,是一體的東西。所以,在靜的狀態來講,沒有一觸而發的情況,本來「不觸」也無所謂,但是有了觸之後,它就顯出它特殊的功能,就產生一個我的覺醒。而這個我的覺醒所需要的內、外六入的基本配備,又已經在那裡了,才能夠產生這個作用出來。所以,換句話說,觸就以六入作為它的根據。
六入是一種很粗顯的設施,很明顯地,耳朵、鼻子、眼睛都已經分得很清楚了,毫不含糊了。可是任何粗顯的設施會形成,有它更細的道理在;也就是說,一個粗的東西會形成,一定有它更細的東西在裡面。因為有這個更細的根據在那裡,才會形成內六入和外六入這麼一套設備出來。這個設備是根據什麼而出來的?推想回去,它裡面有一個更深的依據。
這個更深的依據,無非是所謂的「能詮」和「所詮」。何謂「能詮」和「所詮」呢?「能詮」,就是能夠詮釋,「所詮」,就是能夠被我們所詮釋;或者說,所謂的主觀,我們把它叫「能詮」,所謂的客觀,我們把它叫「所詮」。所以這個更深的依據,亦即是主觀和客觀的基本差異。
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我是主,他是客?因為我們有一個作用,好像可以解釋那個外在的境界。在這樣的差異限定之後,才界定了我們的主觀與客觀的界限;如果沒有這一層差異,無所謂主觀與客觀。換句話說,能夠形成這種很粗糙的內六入與外六入,其基本的較細層面意義,在於一個基本的差別,就是主觀和客觀的基本執著或觀念在裡面。
「能詮」另外一種講法,就是能夠表相 │ 可以表外界的相。這個可以表相的內容,也就是「名色」的名;同理,「所詮」就是能夠被表相的境界,也就是「名色」的色。因為能、所互相緣起,「能詮」與「所詮」也因此保持著一種對立又互相緣起的狀態。這樣一種對立差別相,我們叫做「名色」,而如上述,名與「能詮」同義,色與「所詮」同義。
能所的對立
名既然是「能詮」,能夠表相,就是一種精神的作用,也就是一種心的作用。心的作用,因為被看作是一種主觀的作用,所以客觀世界的凸顯,即被看作是沒有心的作用。亦即是說,「能詮」的「名」一在心中作用,「所詮」的「色」 ─ 客觀的、沒有心的作用的境界,即被詮釋。
觸所依賴的六入,其根基即在這個很細微的「名色」所建立的微細對立上。「名色」的微細對立,它的依據又在什麼地方?想去分別「能詮」或「所詮」,必須知道不但我能詮,而且還可以詮「所詮」裡面各種不同的差別相。所以,這一套系統,要能夠建立起來,它更深的基礎在差別相。也就是說,在我們開始有主觀跟客觀的分別前,這個世間已經在分別了 ─ 已經有了這樣、那樣的不同。如果沒有這樣、那樣的不同,怎麼可能從裡面建立一個主觀或客觀呢?如果這個世界是統一的,我們根本無法去分別這一個東西,那麼這個時候,會不會有「能詮」跟「所詮」之別呢?不會有,因為至少要有二個,才可把A叫做「能詮」,B叫做「所詮」;如果一個分別都沒有的話,不可能建立「能詮」跟「所詮」。所以在這個意義之下,主觀與客觀的對立,有一個更深微的基礎,就是這個世間,已經存在了一個差別的現象、概念,這個差別相的形成,就是透過識。亦即是說,「名色」能產生「能所」這樣的對立,它更微細的地方,在於先要有一個區別,因為倘若一個區別都沒有的話,遑論「能所」。「能所」本身是一個區別,所以先要有一個差別作為它的基礎,然後從差別的狀況裡邊,把這個叫作「能」,而把差別外的對象,叫作「所」,這樣子,「能所」才能建立得起來,所以「能所」的基礎,在於產生識別作用的這個差別。
差別的虛幻
「緣識而有」,識就是區別,也就是把它分別出來之意。此處之識,不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六識,也不是第六識的意識。它有更深細的意義,就是它沒有主客的對立,它只是顯現一種差別,而不去管這個差別裡面,什麼是主,什麼是客。因為它不管這個差別問題,所以它在比「名色」還要更細的一個層次。
這樣的差別,如何去顯現出來?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?這裡已經到了非常微細的地方。從佛的境界上講,緣起的觀念「此有故彼有,此無故彼無」,彼此互為存在的條件,意謂不可分的境界。如果我們互為存在,則不能在我的這一面,把你踢除開來,也不能從你的這一邊,把我踢除開來。所以,互為緣起,表示這是一個不可分的世界;這一片緣起,我們叫做「如的世界」 ─ 如是如是。
在這一片「如的世界」裡面,它一方面緣起,現出差別相,好像可分;一方面透過緣起,又是沒有差別相,不可分。所以,它的這種差別,正是顯現它的無差別;在不可分的意義上,它是一個整體,一個無差別,而它的無差別,正好可以彰顯它的差別相。這是非常深邃的道理,一個如來證悟的世界。但是,在這一種如的狀態裡面,為什麼會產生識的分別呢?因為識的分別裡面是帶著錯誤的,一路過來都是帶著錯誤的,即是說識所產生的分別相,不是一個合理的分別,它是帶著執著,認為這個跟那個是不一樣的,不認為這是一個如的世界,因而破壞了這個如的世界,產生識的分別。
但是,為什麼會在一片「如的世界」裡面,產生這種錯誤的「識的分別」呢?因為這種分別本來在我們這個緣起的世界,並不是不可以顯現分別,但是這個「如的世界」裡,所顯現出來的分別,本質上是不可以分別的分別,如果硬把這個不可分別的分別,當成是可以分別的分別,這就是一個錯誤。這樣的錯誤一形成,就滲出識的世界。所以,能夠使得識產生一個錯誤的執著,它必須要有前面一個錯誤,這個錯誤的行為,就是「行」。
差別相的造作
識會把一個無分別、如的世界,看成是一個可以分別的世界,這個原因的根柢,就在於識做了一件錯誤的事情,叫做「行造作」。本來如的世界裡,是這麼一個平等的世界,忽地差別相現起了,行就現起了,它的根柢裡面,雖然也是無差別的現起,可是如果我們在這個上面,把差別相稍微把握、留住、或注意了,立刻使得這一個被我們特殊注意到的差別相,顯現跟其他的相不太平等的樣子。換句話說,原來這麼平等的、沒有問題的世間,因為我們偶而注意到這一個相,而有了差別。因為太注意這個相,所以這個相,好像變得跟其他東西不平等;或者說,因為太注意這個相了,就慢慢地看出這個相的次第變化,感覺出這個相的次第相續性,這樣的錯誤,就是行的表態。
這樣的解說是什麼意思呢?就是說,識別產生這樣的一個差別,在佛家的觀點來講,始終是一種虛妄的差別與對立,都只是我們在虛幻的世界裡面,主觀上的一種錯覺;這錯覺裡邊,就把它提出來一個「行」,其意義即是造作,也就是說,把一個東西加以認定。譬如說,在現實的世界中,我們知道大跟小是對立的,所以大跟小只有在相對之下才有它的意義。假如我們忽略掉大與小這樣一種相互緣起的關係之時,恍恍惚惚我們就會認為「大」就是一個很真實的大,好像這個「大」不需要「小」來陪襯它,它就可以單獨地存在。當一有這樣一種感覺的時候,這個「大」就被落實了;本來是一個不實在的「大」,忽然間從這裡邊,這個「大」就變得很實在。這樣一種過程,就是一種「行造作」的過程,使得本來沒有意義、空洞的一個「大」,好像恍恍惚惚地,產生了它實質的意義出來。這個實質的意義不是它本有的,而是被我們造作出來的;一旦我們造作出來一個好像比較實在的「大」之後,這個大就開始有了它的生命。因為在我們的觀念裡,一個實在的東西應該存在下去,而且應該連續地,在不同的「剎那」裡存在。所以這個造作之後,就不可避免地,產生一個「時間相」出來。所謂「時間相」,另外一種說法就叫作「遷流」,所以「行」有二個意義:一個叫作「造作」,一個叫作「遷流」。從這個觀點來觀察,實際上造作就是遷流,因為這個遷流原本就造作出來的。
那麼,為什麼要產生這樣的造作呢?如果這個世界,是在一個理性的狀態裡,對大與小不再那麼執著,不再覺得大跟小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情,或覺得大跟小實際上是一件事,只是我們從兩個地方去看它而已,那麼,大的內容裡面,需要小來陪襯。如同走到小人國裡去,覺得人人都很小,那是因為用我們自己的身量和身材跟他們作比較,他們才叫作小;假如我們也化身到小人國裡去,而忘掉我們的過去,這時我們不會覺得小人國的人小,我們會覺得小人國裡,還有我們覺得很大的人在裡面。所以如果在這樣的一種觀照之下的話,我們大小的觀念就不再那麼強烈,開始慢慢地,就消融掉了。然而不幸的是,在一種曚昧的狀態之中,忽然間,我們失掉這種理智的清明,覺得這種東西就是大,大就是很大,大就是好,所以,大就是我要的,小不是我要的。在這樣的處理之下,大與小之間,不知不覺地又作了很大的區分,這樣就開始了「造作」。所以當念頭住於一境(念頭更微細的地方就是住於一境),會凸顯了某一種最深處的一念錯誤,亦即「無明」,使得我們能夠造作,也因為有這樣錯誤的行,其錯誤的識的世界才會顯現出來。
苦的根源
這個形成錯誤的行的無明,不是見思無明,也不是塵沙無明,這樣講的無明是根本無明 │ 最深最細的無明。一片「如的世界」中,嘎然注意到這個「相」,注意再注意,好像顯得它跟其他的相不同,為什麼會突然間注意到這個相的差別呢?就是這個最深層的無明在作祟。
為什麼是根本無明?因為有無明的一動;就是開始有那麼一點從微細到很微細的差別,當注意到它,還沒有仔細地去分別它時,已經是差別了。就這麼一動,無明即現起,差別相立現;也就是說,無明就在那一動的剎那。這一動,並沒有很複雜的念頭,它沒有這個與那個之別,一有差別已經是很粗的無明,即見思無明。現在講的無明,是稍微地注意一下,這一注意造成了錯誤的行;一造成了錯誤的行,即展開了時空。因而可知,在錯誤的行之下,才有幻覺的時空出現;而這個時空,一方面成為我們的幻覺,一方面經由錯誤的行導引,識才有可能產生時間這個東西出來。
無上微妙的深觀緣起
如此從比較深刻的地方來觀察十二緣起的話,這個十二緣起所表現的意義就完全不一樣。這樣子的解釋,不需要三世,從一念的無常之苦,就可以回溯到根本的無明上去;根本無明其實並沒有離我們很遠,所以,不要說根本無明是一個無始無明,雖然我們不懂得什麼叫做無始,可是想像起來卻是很久遠的事情,與近在咫尺的根本無明不太相應。換句話說,在當下的心念之間,不管這一念是愛,還是要取著的心念,或者只是一種感受,在這一念之間,實際上已經俱備了它源頭的無明,因為如果這一念沒有無明的話,這一念的觸、受、愛,就不會造成苦果,它會是一個清淨;但是我們這一念的受、愛、觸並不清淨,因為有執著在裡面,也就是說,這裡面有一個無明的條件存在。在這樣的一種意義下來講,這個深觀的十二緣起,可以是一念之間的十二緣起,不管心念是怎樣一個動法,只要心念一動,就帶著執著,帶著錯覺,那麼這一念之間就含蘊了過去的無明,與未來的生跟老死在裡面。
雖然時間的遷流相,只是我們行的一種造作,使它現出這種遷流的時空出來,但是有時候,在這一分鐘裡,我們從這個受裡,好像因為前面的受,表露出一種愛惡出來,從「時間」上看,就出現了一種因果的關係在裡面。從一念的觀念來講,這一念的受,自相應到這一念的無明,另一念的愛,又自相應到另一念的無明。也就是說,其實這十二緣起本身並沒有時間的次第,在這一剎那,它凸顯出十二緣起的某一支;在下一剎那,又凸顯出十二緣起的另一支。因為這種凸顯,只是它的一種現起,時間的觀念就被消化掉了。這裡最難理解的地方,就是時間是我們在一種無明的狀況之下,給它設立的一種架構。因為這是我們設立的一種架構,好像在這個「迷」的中間,有時間的次第,而這個時間次第實際上也就是一個因果次第。所以,因果的關係,是我們在無明之下所賦予它的一種關係,並不是說有一個「時間」在那個地方,然後我們在時間之流裡,像流水一樣順著流過去;而是整個十二緣起,如果從深觀的角度看,就是一套無明的系統在時間中展現,而變成了我們的生活。所以生活是我們把它放在時間中去展現,並不是它先天俱備了「時間」在裡面。
「時間」與「時間相」的區別不容易理解,但我們可以從電影與影片來想,幫助領會。看電影時,因電影之情節,會覺得有一個時間在流動,可是一卷影片擺在那裡,沒有去放映它的時候,它並沒有時間,沒有人會覺得那個影片有生命。但是如果我們順著這個片子的順序,次第地給它排列出來的時候,忽然感覺到影片裡的東西活起來了,好像有時間了;可是如果不把它放在放映機上演一遍,而是收在箱子裡面的時候,那卷影片上有時間、因果、先後、長度嗎? (只要有時間定有一個長度) 在電影放映的二個小時內,可能電影情節裡的時間是十年、廿年;不管是二個小時還是感覺的十年、廿年,它都有一段時間過去。可是這一段東西當我把它放在一個膠卷盒子裡的時候,從那裡去找個十年?或從那裡去找那二個小時?
不管是深觀或淺觀的十二緣起,要了解,深觀和淺觀並不是兩樣事情。當深觀這個緣起的時候,好像是把一個影片放在這個地方,沒有去放映它,而靜態地、作整體性的結構觀察;淺觀時,就像把這影片放到放映機裡放出來,它就明顯地產生因果次第與時間結構。
從這樣深觀的十二緣起來看,緣起的甚深含義才比較能彰顯。因為緣起的本意,就是「此有故彼有,此無故彼無」,也就是這個世間,過去與現在,原來是互相在緣起,時間在這裡就被化掉了。時間沒有化掉的話,表現成一種不可逆的因果關係;時間一旦化掉的話,這個緣起的世間不是只有這一剎那間的緣起,而是三世的緣起 ─ 過去、現在與末來一同緣起成這樣的世間。
雖然時間化掉了,就某種意義來講,這裡還隱含有時間「相」。這個「相」的存在,可以讓我們有更高的思考層次,去把時間相破除。如此去推論的話,雖然不敢說登峰造極,但卻提顯了一條很遙遠,可以直通「甚深佛意」的道路。因為這種由苦的根柢,找出苦的根據所在,進而把現實裡能夠產生「我執」的根源,一一有順序地倒推回去而導出的十二緣起觀點,才比較能相應到甚深的緣起理論上去。佛當初證悟的十二緣起,如果談的是內證的境界的話,毫無疑問地,是一個很深的緣起,可直接相應到所有高層的佛學裡面去。所以,雖然十二緣起是原始佛教的重要環結,偏屬於小乘的範圍,但是,深觀的十二緣起不是談小乘的十二緣起,而是談直通大乘的十二緣起;這個深觀緣起的理解很重要,因為諸多宗派的緣起理論均以此為基礎。
深觀十二緣起對緣起學說的重要性
我們知道佛法是講緣起的,無論大、小乘或各宗各派,緣起都成為其最中心的學說部份,而十二緣起與每一個學說均絲絲入扣。
業惑緣起
淺觀的十二緣起立場,有一個名稱叫作「業惑緣起」,日本人叫作「業感緣起」。所謂的業惑緣起,就是認為我們這迷惑、痛苦的生命流轉,基本上就是三件事情在流轉:一開始有了無明的迷惑,由於這個迷惑,使得我們作出一些不如理、不合理的行為,行為的結果就是所謂的業;由於我們的惑製造了很多的業,在現實的生活中發生效果出來,就是一個苦的世界。不管是我們的生命,還是所面對的世界,由於一受苦,立刻想要解這種苦,於是就再去造業;這樣子造的結果,又轉生出更多的疑惑。就像吸毒一樣,想要得到樂一點的感筧,所以去吸這個毒品,毒品吸完了之後,讓生理上的腦神經受到破壞,心理上則入到一種恍惚的境界裡去;這樣一來會繼續發展出更多錯誤的了解和感受,這就形成「惑、業、苦」的流轉。
在淺觀的十二緣起裡,把惑、業、苦展現得十分明白,亦即過去的無明 (惑) 造成過去的行 (業) ,然後造成現在的識、名色、六入跟觸、受 (苦) 。受了苦卻不知道苦,所以繼續地造作,於是有了這個愛、取。這個愛實際上又是一種迷惑,有了這個迷惑又去取,這個取則是一個新的業。然後又產生未來的有、生、老死,又是一種苦果,這就是以淺觀的十二緣起來看「惑業苦」的緣起。
這個「惑業苦」緣起,從淺觀的觀點看,還是從一個現象上來看緣起。但是在這樣的緣起裡,為什麼我是我,你是你?為什麼我作的事情要我來受,而不是你來受呢?在淺觀立場上來講,仍然有三世流轉,那麼為什麼這個東西可以從前世帶到這一世,又帶到下一世呢?這些東西,從現象上看,淺觀的十二緣起無法解釋何以這樣的惑、業會帶到今生,再帶到下一世去;或者說,從上一個剎那,帶到下一個剎那。從這個方向繼續去發展,為了要把這些惑、業能夠流轉的基礎找出來,就成了所謂的「阿賴耶緣起」。
阿賴耶緣起
淺觀的十二緣起只有六識: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,前面五識都是我們的感官,很粗淺,不用則無感覺,譬如我們不用眼睛的時候,眼識就停止了,不用耳朵聽的時候,耳識就停止了。因為前五識都會中斷,顯然就不適合作為攜帶業果的基礎,所以在六識裡,可以考慮擔任這個角色的,唯有第六識。
第六識非常地特殊,也非常地靈敏,它通於我們內在的精神,也能夠透過我們前五識的協助,接觸到外在的境界。但是,這樣一個第六意識,能不能作為基礎呢?還是不能,因為第六意識也會突然停止,譬如有人突然昏過去了,過了兩三個小時,他還不知道已經過了兩三個小時,換句話說,在這段昏厥的時間,第六意識是停止的狀態。可見得,第六意識並不是連續的東西,它在時間之流中,也是會中斷的,所以也不能擔負攜帶業果的責任。在小乘佛學裡,因為只談六識,所以在討論這個問題時,就想辦法創造其它的角色出來,譬如有些人就製造出「我」的觀念,另一些人就製造出一種叫作細意識的,就是說,勉強地在第六意識後面,認可一個很微細的,平常沒有感覺到的東西。這樣的觀念,後來慢慢地發展,就成了大乘裡法相唯識宗的「八識」的觀念。
「八識」就是除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識之外,加上第七識,名為「末那」,又加上第八識,叫作「阿賴耶」︵簡稱賴耶︶。雖然分成八識,其實它的重心是在第七、八識上,因為六識中,沒有一個可以作為因果或業果傳遞的主體,必須是在六識之下,還有一個更深刻的識。這個識雖然還是「識」,可是它的分別力非常地微細,前六識沒有辦法感覺到它的存在。這個識不像前六識一樣會間斷,雖然它的作用非常地微細,可是它卻是不間斷的。這裡面當然牽涉了一大套的學問,譬如說所謂的「不間斷」,是「不斷不常」,不是我們想像的永恆,但是它又不會間斷,那它是什麼呢?這就有如流水和瀑布,長水大河好像是一個連續的東西,但是仔細看看,它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個流動的東西,換句話說,這流水的每一點都是新的一點,而新新不已。所以從新新不已的觀點來講,它是無常的,因為它沒有真正的不變過,它永遠在變;但是從相續的觀念來講,可以說它是不斷的,「抽刀斷水水更流」,沒有辦法把水切斷旳。藉此譬喻,可以瞭解七、八識也像這個流水或瀑布一樣,沒有間斷,但也不是恆長。
七、八識概略說起來是一體的,但為了要解釋意識之中的我執,所以建立了第七識。譬如說我們平常有一種我執,感覺有一個我的概念在其中,這個是第六識裡的我執;可是當深度的睡眠或是昏倒,第六識不現形的時候,我執是不是就斷掉了呢?如果我執可以斷一個鐘頭,應該我們就可以解脫了,也許不要斷一個鐘頭,說不定一分鐘,我們就解脫了,就開悟了,但是我們沒有開悟,沒有解脫,這表示我們的第六意識中斷的時候,還有一些微的我執在那裡,持續不間斷地產生一種執著。
第七識跟第六識的我執不一樣,第六識的我執是很粗顯的,但是會間斷;第七識的我執是不明顯的,非常潛在的,有時候我們說,修行了大半輩子,怎麼忽然就發脾氣了?雖然很清楚不應該發這個脾氣,可是這個脾氣發得沒有來由,而且發得很強烈,所以必然有比我們第六識更深細的一種分別或執著在裏面。這就是第七識的功能,它不斷地在那裡執著一個我,執著什麼東西是我呢?它執著的就是阿賴耶,嚴格地講,它執著的是阿賴耶裡的一個見分,但大略地講,就是因為這個阿賴耶在某種意義上有一個不斷的性格,維持了某種恆長性,像我們的流水一樣。
由於有這樣的相續性,阿賴耶識才有這種不斷不常的恆長性在裡面,因此第七識可以把第八識想像成是一個「我」,這是第七識的一個功能。這樣的解釋,的確在世界的發生和現起,以及知識方面的過程,都比小乘的淺觀十二緣起精確,而與深觀的理論相應。若更細一點分析,第七識對阿賴耶見分的執著,本身就是一個十二緣起的現起;雖然已經是如此地細了,在第七與第八識內的見、相二分的剎那,以及在第七識執著第八識見分的剎那,十二緣起的每一支,支支分明。(寫到這裏,忽爾嚎啕大哭,感歎佛陀所證悟十二緣起的深邃,對佛慈悲示現的恩典,無以回報,真是汗顏報憾,淚流滿龐。是為記。 )
對「賴耶源起」有了這樣「深觀的十二緣起」的理解,其實已經進入「真如緣起」,甚至很直接地相應到華嚴境界的「法界緣起」或「無盡緣起」,乃至於天台的「一念緣起」。這就是為什麼十二緣起應該有深觀的一面,因為深觀的十二緣起直接相應到「法界緣起」跟「一念緣起」,這樣子我們才可以說十二緣起甚深。
修行的緣起觀
不論淺觀或深觀,說十二緣起的目的,都是為了要說明為什麼我們當下的存在要這樣子存在,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苦,以及苦的生命是怎樣子形成的。我們已經理解到這樣的一種存在是苦的存在,我們也看出了苦原來是這樣子緣起而出現的。不管從深觀或淺觀的角度,我們都得到了一個不同但很具體的概念,在深觀上我們了解,在這一套緣起裡,此有故彼有,所以一旦有了一個,其它就全部都有了;在淺觀裡,我們瞭解時間是因果的鎖鏈,在這個鎖鏈之中,如果俱備了前緣,就逃不掉後面的結果,因為它有個限制性在裡面。
生命的流轉
我們的生命,如果從淺觀的立場上講,是被束縛住了,因為不管從二世還是三世來看,過去已經有了「無明」和「行」,這件事已經是個無可更改的事實,我們又不幸入胎生下來了,俱備了這樣一個身體,從這個身體上我們又很自然地產生了「觸」,又得到了受,而對這個受產生了一種執著,從這個受的執著裡,又發生了「愛惡」,因為愛惡的關係,有些是我們喜歡的,有些是我們討厭的,於是就爭取或排斥,所以這時我們又產生了「取」。這個生命,一旦流轉,就會如此無可奈何地,輾轉產生今生的生、老死,或來生的生、老死,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。所以觀察這樣一個現象,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:生命如果不作任何努力的話,順著這個十二緣起流轉下去,將是一個無盡無止的流轉,而沒有任何的出路,這個現象,我們在佛學裡面就叫作「流轉門」。
解脫的還滅
生命既然是以這樣的因緣與次第在無盡地流轉,那我們有沒有希望可以從這個流轉裡頭解脫出來?這是我們學佛真正的問題所在,其中心的目標,就是希望能透過這個流轉的解析,找到一個解脫的方法。這解脫的關鍵或法門,將使得我們這痛苦流轉的生命可以停止下來,得到一種休息,這條路就叫作「還滅門」。
流轉與還滅
研究生命與解脫,要同時從這兩個角度,一方面看流轉,再方面看還滅;也就是說,瞭解了生命的流轉之後,要從這樣的流轉裡,找出還滅的契機在何處,這就是修行人要把握的中心。
小乘的修行:從淺觀的觀點來說,因為有時間的先後與三世的因果,緣起雖然也有無明作為它的基礎,但卻是過去生的無明。我們不能像走時光隧道一樣,回到過去生,再去修正過去的「無明」跟「行」,同時也無法變動父母給我們身體的「識」、「名色」與「六入」。再者,因為未來我們無從接觸,未來的生跟老死,那是未來世的事情,也是我們想要把它解脫的事情,所以也不是我們能夠著力的地方。因此如果把十二緣起,連頭帶尾地,丟掉這些無能為力的支,我們還剩下什麼呢?只有「觸」、「受」、「愛」、「取」、「有」。
在這五支裡,雖是我們現在生的,但「有」是「取」的一個結果,因為有了這個取造成了這些事情,它已經留下了一些因子,使得產生未來的苦果,儘管這個苦果一時之間還沒有現起,但是這個根已經種下去了 │ 沒辦法把已經得到的根,再把它重根挖掉。所以這裡面,真正讓我們感到還可以處理的,只剩下「觸」、「受」、「愛」三支,可是在觸的地方時間很短促,因為在一觸之下,我們也已經不能再回頭了,也不能防止繼續地再生觸,所以「觸」這一支也不太能夠著力,如此一來,最後只剩下「受」跟「愛」這兩支。
「愛」與「受」成為我們今生需要著力的地方,但是這個「受」裡所產生的苦、樂感覺,卻是受了我們過去的習氣與因緣而現起,往往也是很不由自主地,所以在這僅剩的兩支裡,第一個我們要把握的,就是愛這一支。當我們有了苦、樂的感受,或如意、不如意的感覺,在要產生慾望的時候,可以稍微留意,再等一下;這裡是十二緣起中,唯一還有時間讓我們再等一下的一支。「等一下」的意思是說,根據十二緣起旳道理,假如現在有了受,但不因這個受而產生慾望去追求,或者去排斥,那麼就不會因為這個受帶來一些更多、更複雜的行為出來。這樣子的話,在往後的緣起上,就不會再有新的結果出來;所以在這個意義下,雖然我們不能夠把緣起斷掉,但是至少我們已經可以控制這個緣起。
這樣子的思維,就產生了小乘修行的哲學,以斷愛慾為主,換句話說,根據十二緣起的反省,只有在受跟愛這個地方可以著力,而比較容易而有時間著力的地方,就是愛這支,因此要用種種的道理和戒律方式,使之了解,不要去順從自己的慾望,要把慾望降到很低,甚至於沒有的程度,這樣子就可以在某種意義下使十二緣起的鍊子切斷。如果我們真的把愛斷乾淨,則不是在斷一種慾望,而是在斷所有的慾望,那麼結果就不一樣了,因為在斷盡所有的慾望之後,任何的取都沒有辦法發生,這時候因緣的鎖鍊就斷掉,這個在小乘佛法裡,就是得到了解脫 │ 一種究竟的解脫。
斷愛慾更好的方法是,更進一步去控制受,使在受的地方得到一種平和的受,在修行的層次上,若到了這麼一個狀態,就是任何的受不會變成一種強烈的感受,這樣子就根本連愛的機會都沒有了,所以更徹底一點。這樣的看法,在小乘裡就是他們「還滅門」的看法 │ 如何斷掉愛慾。
大乘的修行:從深觀的觀念來講,這個十二緣起「一有一切有」;同樣地,依照深觀緣起的觀點,也可以「一無一切無」。既然老、死跟著「無明」、「行」纏結在一塊兒,如果在這個十二緣起裡,能夠在一念之間把緣起的條件變動,庶幾乎我們可以跟「十二緣起」不緣起,也就是「一滅一切滅」。在這樣的深觀看法裡面,整個十二緣起是在「無明」下面,因為我們了解到,這整個的根,是有一個錯誤的「無明」在這個地方;我們又了解,我們的念念都俱備十二緣起,所以我們念念之間都有無明。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在這一念之間把握得好,使這個無明不起,至少我們是一念的解脫,假如我們能夠念念的無明都不現起,那就是念念的解脫。這就是阿彌陀經所說的「一心不亂」與「心不顛倒」的真諦,也是禪宗行者參話頭的用意。
緣起觀的「理」與修行的「事」
不論小乘或大乘,深觀或淺觀,在對緣起的「理」了解以後,我們已經找到一個修行的方向了,照理說,可以開始修行了,但是我們還需要多了解一下。雖然在理路上我們有了一個脈絡,但是「理」跟「事」都要能照顧到,才不會執事廢理,或執理廢事,因為這個世間是一個「理」跟「事」都存在的世界,所以如果只看理這一邊的話,有時候會陷入一個迷惑裡去,所以我們在看過「理」後,要回過頭來看看這個「事」的世界是怎樣的世界。就是說,我們講三世,也講輪迴;但是輪迴並不是每個人都清楚,在學佛上,它跟我們的修行又有很深的關聯和意義。從覺悟的觀點講,本來我們也是應該要多了解一些宇宙裡面種種的現象,因此對「宇宙有情狀況」和「宇宙器界概說」,就不能不下點功夫去研究。能夠如此把握,學佛的道路,才算真正地確定。
前期談十二緣起,涵蓋了兩種說法:第一種是一般的說法,就是把十二因緣劃分成三個階段 ─ 過去生,現在生和未來生的「三世」。三世裡從過去因到現在果,然後從現在因到未來果,構成了雙重的因果關係,所以叫作「三世兩重因果」。第二種是藏傳佛教的說法,把無明從死亡的剎那來說,也就是指我們在死亡的過程中間,有一段黑暗時期 ─ 是真正的黑暗,物理上的黑暗 ─ 這個黑暗時期,即是一種無明。從這樣的無明開始,就進入中陰的階段,所以在這個說法裡,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,乃至於觸、受、愛、取,全部表現在中陰身的階段裡,「取」和「有」兩支就相當於入胎和住胎了。剩下的兩支,「生」就是真正的生出來,以至於今生的「老死」。這種說法是從過去生的死亡剎那算起,到這一生的老死,只講一重因果。
這兩種說法都屬於一種較淺觀的層次,仍舊沒有離開時間的架構。
深觀的緣起說法
這深觀的十二緣起,不需要追溯到二世、前世,或者是更前世,它只是把人生痛苦的現象,用十二緣起的方式把它展現出來。也就是說,生命從無常的觀點來看,一切的受都是苦,沒有所謂的「樂受」在其中,當然,這個苦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定義,也就是「一切皆苦」的苦,實際上,它真正的意義,並不是一種感受性的苦,而是一種本質性的苦。只有在本質性的苦上,我們才可以瞭解人生的一切都是苦的。在這深觀的緣起說法,主要彰顯的是,我們現在之所以會產生「愛」、「取」這種不應該的執著,其根源即在於有一種「我執」。但是,「我執」的根源又是什麼呢?在佛家的語言來講,「我執」是一種「能所」的分別,也就是一種「主客」的分別。換言之,「我執」是因為「能所」產生對立以後,才有「我」的概念,或者說,因潛在的意識存在,這個「我執」要追究到「能所」才能開始有所瞭解。然而,這個「能所」平常是在一種很曚昧的狀態裡頭,往往會忽略掉這個「能所」,好像有點「忘我」,一下子之間,不太覺得外在的世間,跟我們有什麼差別,可是,在一「觸」之下,會使得「能所」的關係突然醒覺;也就是說,在未觸之前,雖然是一種曚昧的狀態,不太有很明顯的主客意識 (雖然它是潛在的) ,但是透過觸以後,這個主客的意議就醒覺出來了。這個主客的意識一醒覺,就開始產生很自然的「愛」、「取」、「有」和下面這一套:::於是一步一步地,會發現有很多的「我執」在前面,輾轉地緣起了這些苦果。如果這樣子回頭去看,就可以把這個十二緣起,由老死、生、有::到無明,從反方向找出「苦」的中心所在。
老死諦
老死可以看做是對無常與苦的總結,為什麼呢?因為老死所詮釋的就是一個很明顯的無常,而無常又是苦的中心含義,所以老死無非就是講我們當前所受的一切苦的總稱。從另一個角度看,老死並不要等到二十年或三十年後,我們分分秒秒都在老死中。所以佛說人命在呼吸間,不是說我們可以再活個幾十年然後去死,而是說我們分分秒秒地在死。是什這個老死或無常的現象,為什麼會存在呢?它的依據麼?
無常的開始
一切的現像,我們能夠談它的無常,它必定要有一個開始,而這個開始的現像會消失掉,然後我們稱之為無常。由此可見,老死的根據,就是有一個東西會現起,會生出來,因此老死的根據在『生』。也就是說,從老死裡面我們體會到會有無常的苦果,是因為我們曾有一個生命的現起。不僅是這一期輪迴的生命,我們現前當下的生命在剎那剎那地現起中。如果我這個生命在下一個剎那不再現起,對我來講,老死或無常都沒有意義。而正是有剎那剎那的生生,於是有一再一再的無常。
剎那的現起
老死若這樣地反省,它的根據在生。為什麼會有生呢?為什麼我能在時間之流裡,剎那剎那地現起呢?其根據就是先要有一個很現實的存在 ─ 一個「存有」。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現實的存在或至少是一套存在的規範,我也好,外境也好,都無從現起,因為根本什麼都沒有嘛!所以這個成為生的現起,必須要有一個存有的依據,要有一套現起的規範。
存有的最後依據,當然是這整個一般性的存有,但自這一般性的存有中,如何表現出我們個人獨特的生命,這或者是一套獨特的存有,或是一套獨特的現起規範。那是什麼呢?就是前表讀過的五蘊 ─ 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我們存有的基本形式便是一個「五蘊的存有」。而我們前面也說過,這個五蘊的存在,不是一個只有主體性自我的五蘊,這個五蘊是涵蓋著客觀世界的五蘊,是主客在一體的五蘊。在這樣一個「大存在」裡面,心怎麼去想,怎麼去受,怎麼去識,色怎麼定位,都有它的分際和限制在裡面。也就是說,這樣一套東西,有這樣一套運作和現起的規範,我們才有這樣相續現起的生命,才有不斷的生生。
老死:無常與苦
<
生: 無常的開始
<
有: 存在及其現起之規範
<
取: 五取蘊的執著
<
愛: 我執的凸顯
深 <
觀 受: 主客的凸顯
的 <
緣 觸: 主客的覺醒
起 < 六入:配備的齊全
<
名色:能所的對立
<
識: 差別的虛幻
<
行: 差別相的造作
<
無明:苦的根源
五取蘊的執著
然而這五蘊的規範,不是哪一個超越的主宰幫我們訂下來的。從五蘊的內容,可以瞭解到,它是透過我們的「識蘊」裡分別識的架構系統,然後再透過「行蘊」裡面的行的造作,才把五蘊這樣子展佈開來;這個識之所以要這樣分別,或行之所以要這樣造作,其背後就隱藏一個我們的執著。不是誰要我們去造作、去分別,而是我們自己要這樣去造作、去分別,所以我們的五蘊又叫做五取蘊。換句話說,這個五蘊,並不是個客觀的五蘊,它不是個「你理它不理它,它都會這麼存在」的五蘊。不,它是在深層意識的執著下這麼選擇,規定而成就的五蘊。所以,這個五蘊是「取」而來的五蘊,是依照我們執著地取,而成執著的存在。
所以「生」所根據的這種「存有」不是個客觀的存在,而是透過「取」,而形成的五蘊的存在。這個取,是一個錯誤的取;是一種帶著我見 ─ 法我見與人我見 ─ 的取。這種不斷地、錯誤地執取,它的根源一定要有一個動機 ─ 我怎麼會一直去犯這個錯誤?而又有什麼力量,推動著我繼續這樣地去取?這個根源推究起來,必在於一種強烈的欲望,也就是所謂的愛。欲生一方面會矇蔽我們的理性,而同時又能發出很大的作用力。
我執的凸顯
愛是一種希求,一種渴欲。它的本質還是貪。在世俗的看法、都認為欲望或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。有愛有恨,甚至敢愛敢恨,似乎唯其如此,人生才有趣味和意義。佛學看愛,這件事誠然沒有這麼高的價值,但也同意,是愛規定了我們的方向,不只是所謂人生的方向,而是整個生命的現起。愛除了表現成對外境粗顯的愛惡外,更深、更強而也更不易感覺的是那種對存有和存有的延續之愛。細看愛的狀態,常是很繃緊的,深切期待的,甚至是強迫的。愛越強烈,則緊張的程度也越高。為什麼會如此呢?因為愛的結構裡必然地要充分肯定一個能愛的自我和所愛的外境。對兩者愈認真,對愛的情緒也愈強烈。所以就這一重意義而言,所謂愛不過就是我執,包括人我執和法我執的高度凸顯。在這種愛的籠罩下所現起的取,當然也就成為一個錯誤的執取。
這樣一種愛的狀態是如何起來的呢?也就是說我執會凸顯或放大,它的基礎和條件在那裡?執著的根據必須要先有主觀和課觀的對立,若無明顯的主觀,執著便無從談起。而凸顯這一主觀意識的便是使意識產生內容的「愛」。
主客的凸顯
如果主客之間,不產生如此尖銳化的「希求」對立,則沒有那麼強烈的「取的行動」出來。而這種「愛」的狀,把這個深層的我,突然地勾起來了。所以它的根源在於「受」,而「受」的含意就是把主客之間的對立,極度地明顯化。
本來我見是潛藏的,現在我見透過刺激凸顯了;本來一個我,很小看不見,忽然間,在這一剎那,這個我變得這麼大,這是什麼原因呢?是「受」的凸顯作用。因為我太苦了,太樂了,這個大苦與大樂,把深藏的我,凸顯成一個很大的我。這個受,為什麼能把我見,這樣子凸顯出來呢?它的依據又在什麼地方呢?這個還要有一個前題,就是主客之間,是受到一個外來刺激,所以在心裡的過程上面,這樣一個刺激,在凸顯我見的前面,要有一個接觸。這種內外的接觸,或主客的接觸,就是我們的六根去攝納外面六境的接觸,亦即是根境之間的接觸。
主客的覺醒
態,我們通常把它形容成一種很緊張的狀態 │ 整個心都繃在那個地方。這樣一個「愛」的狀態,是如何起來的呢?一定先要有一個刺激,一個感受。假如坐在那邊安安靜靜地,外界不給它刺激,不會有很強烈的愛要起來;忽然間給了他一個刺激,主客立即對立,這個刺激就是「受」。要有一個刺激之後,才會產生一個很強烈的渴望出來;而渴望的強烈擴張,在於我們把我見提昇到表面層次來,使得主客之間,產生一個緊繃繃的局面,變成二個截然的對立體,好像敵人相見,分外眼紅。所以其根源,是把我見提昇得很強烈,可是我見是怎麼樣子被提昇得這麼地強烈呢?因為受到一個外界的刺激
六根去接觸六境的「觸」,一般的解釋是「接觸」;而真正做為「受」的依據的「觸」,卻有更深的含義。原來,我們主觀的根與外面的世界 ─ 主觀與客觀 ─ 從佛的證境上來講,是一體的,不可分的;亦即是一個覺悟的狀態,本來就沒有所謂主觀與客觀。這種沒有主觀與客觀的狀態,並不因為我們人的執著而有所改變,換句話說,我們可以去誤解這個世界,但是世界並不因為我們的誤解而產生扭曲,世界還是那個樣子,實相還是實相的樣子。儘管我們覺得有能、有所,有主、有客,有人、有我,世界並不因為我們這樣分裂而分裂。要讓主觀的六根與客觀的外境,真正地現出執著上的分別的時候,就是「觸」的作用 。
這種主客覺醒的「觸」的含義很重要,再試著以具體的「身觸」來解說。我們都有以身體去碰桌子的經驗,如果沒有碰觸的話,當然毫無感覺;但是心不在焉地,或專注在做些別的事情,身體碰到任何一樣東西,可以說是毫無知覺。這裡面的受,就是一個中性的受,甚至於無感覺有這個受,也就是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發生。但是一留心受碰的時候,就知道有觸,亦即是說,當一留心,有觸的時候,主客立分,乍然覺醒。這個觸的本身,就是使得在本來沒有主客之分的情況下,忽然之間,讓主客分別的念頭現起。
受所以會表現得那麼強烈,把自我與外界放大,其基礎即在於觸的覺醒;這個觸,產生主客之間一種很明顯的覺醒。忽然間覺得碰到了,如果完全無心的話,手碰上去,也不會覺得手是自己的手,或桌子是外界的桌子;可是開始感覺到有一種感受的時候,實際上已隱涵主客已分,然後才有所感受。所以,這個觸是很微細的,它使得本來沒有主客之分的地方,「碰」地一觸,即刻現起一個主客之分,然後「受」才感受這個東西。透過這個基礎,才有樂受、苦受,才能去更明顯地放大自我,然後才根據這個放大的自我,產生一個強烈地、很緊張的渴望出來。
「觸」在還沒有觸之前,是一種矇昧的狀態,不太分別得出主和客,透過觸,才產生主客的覺醒。但是,為什麼會觸呢?是依據什麼,才有觸的條件呢?無庸諱言,能夠使觸產生一種覺醒作用的前題,一定要有一套基本設施的提供。何謂設施呢?設施就是「既成裝備」,能夠給觸一個機會,產生一個「自我覺醒」,或是「我見覺醒」的設備。有了這麼一個基本設施,觸才可一觸即發,這個基本設施是什麼東西呢?就是我們的內六入和外六入。
配備的齊全
內六入 (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) 與外六入(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) 當初成為基本配備時,並不知何者為因,只知往前面看;反過來說,「觸」能一觸即發,使得這個我覺醒出來,是因為已經有了內六入和外六入的基本配備在那裡,否則無從發起。譬如說,我們已經長好了一個耳朵,長好了一個眼睛,長好了一個身體;而外界又是長好了這麼樣的一個世界,以至於我們有了可以一觸即發的可能性出來。所以觸的基礎,在於有了這麼一個內六入和外六入的基本設施。
雖然我們的設施有內六入和外六入,但是從實相的觀點來看,這內、外並不是相分的,內、外是互相緣起的,是一體的東西。所以,在靜的狀態來講,沒有一觸而發的情況,本來「不觸」也無所謂,但是有了觸之後,它就顯出它特殊的功能,就產生一個我的覺醒。而這個我的覺醒所需要的內、外六入的基本配備,又已經在那裡了,才能夠產生這個作用出來。所以,換句話說,觸就以六入作為它的根據。
六入是一種很粗顯的設施,很明顯地,耳朵、鼻子、眼睛都已經分得很清楚了,毫不含糊了。可是任何粗顯的設施會形成,有它更細的道理在;也就是說,一個粗的東西會形成,一定有它更細的東西在裡面。因為有這個更細的根據在那裡,才會形成內六入和外六入這麼一套設備出來。這個設備是根據什麼而出來的?推想回去,它裡面有一個更深的依據。
這個更深的依據,無非是所謂的「能詮」和「所詮」。何謂「能詮」和「所詮」呢?「能詮」,就是能夠詮釋,「所詮」,就是能夠被我們所詮釋;或者說,所謂的主觀,我們把它叫「能詮」,所謂的客觀,我們把它叫「所詮」。所以這個更深的依據,亦即是主觀和客觀的基本差異。
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我是主,他是客?因為我們有一個作用,好像可以解釋那個外在的境界。在這樣的差異限定之後,才界定了我們的主觀與客觀的界限;如果沒有這一層差異,無所謂主觀與客觀。換句話說,能夠形成這種很粗糙的內六入與外六入,其基本的較細層面意義,在於一個基本的差別,就是主觀和客觀的基本執著或觀念在裡面。
「能詮」另外一種講法,就是能夠表相 │ 可以表外界的相。這個可以表相的內容,也就是「名色」的名;同理,「所詮」就是能夠被表相的境界,也就是「名色」的色。因為能、所互相緣起,「能詮」與「所詮」也因此保持著一種對立又互相緣起的狀態。這樣一種對立差別相,我們叫做「名色」,而如上述,名與「能詮」同義,色與「所詮」同義。
能所的對立
名既然是「能詮」,能夠表相,就是一種精神的作用,也就是一種心的作用。心的作用,因為被看作是一種主觀的作用,所以客觀世界的凸顯,即被看作是沒有心的作用。亦即是說,「能詮」的「名」一在心中作用,「所詮」的「色」 ─ 客觀的、沒有心的作用的境界,即被詮釋。
觸所依賴的六入,其根基即在這個很細微的「名色」所建立的微細對立上。「名色」的微細對立,它的依據又在什麼地方?想去分別「能詮」或「所詮」,必須知道不但我能詮,而且還可以詮「所詮」裡面各種不同的差別相。所以,這一套系統,要能夠建立起來,它更深的基礎在差別相。也就是說,在我們開始有主觀跟客觀的分別前,這個世間已經在分別了 ─ 已經有了這樣、那樣的不同。如果沒有這樣、那樣的不同,怎麼可能從裡面建立一個主觀或客觀呢?如果這個世界是統一的,我們根本無法去分別這一個東西,那麼這個時候,會不會有「能詮」跟「所詮」之別呢?不會有,因為至少要有二個,才可把A叫做「能詮」,B叫做「所詮」;如果一個分別都沒有的話,不可能建立「能詮」跟「所詮」。所以在這個意義之下,主觀與客觀的對立,有一個更深微的基礎,就是這個世間,已經存在了一個差別的現象、概念,這個差別相的形成,就是透過識。亦即是說,「名色」能產生「能所」這樣的對立,它更微細的地方,在於先要有一個區別,因為倘若一個區別都沒有的話,遑論「能所」。「能所」本身是一個區別,所以先要有一個差別作為它的基礎,然後從差別的狀況裡邊,把這個叫作「能」,而把差別外的對象,叫作「所」,這樣子,「能所」才能建立得起來,所以「能所」的基礎,在於產生識別作用的這個差別。
差別的虛幻
「緣識而有」,識就是區別,也就是把它分別出來之意。此處之識,不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六識,也不是第六識的意識。它有更深細的意義,就是它沒有主客的對立,它只是顯現一種差別,而不去管這個差別裡面,什麼是主,什麼是客。因為它不管這個差別問題,所以它在比「名色」還要更細的一個層次。
這樣的差別,如何去顯現出來?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?這裡已經到了非常微細的地方。從佛的境界上講,緣起的觀念「此有故彼有,此無故彼無」,彼此互為存在的條件,意謂不可分的境界。如果我們互為存在,則不能在我的這一面,把你踢除開來,也不能從你的這一邊,把我踢除開來。所以,互為緣起,表示這是一個不可分的世界;這一片緣起,我們叫做「如的世界」 ─ 如是如是。
在這一片「如的世界」裡面,它一方面緣起,現出差別相,好像可分;一方面透過緣起,又是沒有差別相,不可分。所以,它的這種差別,正是顯現它的無差別;在不可分的意義上,它是一個整體,一個無差別,而它的無差別,正好可以彰顯它的差別相。這是非常深邃的道理,一個如來證悟的世界。但是,在這一種如的狀態裡面,為什麼會產生識的分別呢?因為識的分別裡面是帶著錯誤的,一路過來都是帶著錯誤的,即是說識所產生的分別相,不是一個合理的分別,它是帶著執著,認為這個跟那個是不一樣的,不認為這是一個如的世界,因而破壞了這個如的世界,產生識的分別。
但是,為什麼會在一片「如的世界」裡面,產生這種錯誤的「識的分別」呢?因為這種分別本來在我們這個緣起的世界,並不是不可以顯現分別,但是這個「如的世界」裡,所顯現出來的分別,本質上是不可以分別的分別,如果硬把這個不可分別的分別,當成是可以分別的分別,這就是一個錯誤。這樣的錯誤一形成,就滲出識的世界。所以,能夠使得識產生一個錯誤的執著,它必須要有前面一個錯誤,這個錯誤的行為,就是「行」。
差別相的造作
識會把一個無分別、如的世界,看成是一個可以分別的世界,這個原因的根柢,就在於識做了一件錯誤的事情,叫做「行造作」。本來如的世界裡,是這麼一個平等的世界,忽地差別相現起了,行就現起了,它的根柢裡面,雖然也是無差別的現起,可是如果我們在這個上面,把差別相稍微把握、留住、或注意了,立刻使得這一個被我們特殊注意到的差別相,顯現跟其他的相不太平等的樣子。換句話說,原來這麼平等的、沒有問題的世間,因為我們偶而注意到這一個相,而有了差別。因為太注意這個相,所以這個相,好像變得跟其他東西不平等;或者說,因為太注意這個相了,就慢慢地看出這個相的次第變化,感覺出這個相的次第相續性,這樣的錯誤,就是行的表態。
這樣的解說是什麼意思呢?就是說,識別產生這樣的一個差別,在佛家的觀點來講,始終是一種虛妄的差別與對立,都只是我們在虛幻的世界裡面,主觀上的一種錯覺;這錯覺裡邊,就把它提出來一個「行」,其意義即是造作,也就是說,把一個東西加以認定。譬如說,在現實的世界中,我們知道大跟小是對立的,所以大跟小只有在相對之下才有它的意義。假如我們忽略掉大與小這樣一種相互緣起的關係之時,恍恍惚惚我們就會認為「大」就是一個很真實的大,好像這個「大」不需要「小」來陪襯它,它就可以單獨地存在。當一有這樣一種感覺的時候,這個「大」就被落實了;本來是一個不實在的「大」,忽然間從這裡邊,這個「大」就變得很實在。這樣一種過程,就是一種「行造作」的過程,使得本來沒有意義、空洞的一個「大」,好像恍恍惚惚地,產生了它實質的意義出來。這個實質的意義不是它本有的,而是被我們造作出來的;一旦我們造作出來一個好像比較實在的「大」之後,這個大就開始有了它的生命。因為在我們的觀念裡,一個實在的東西應該存在下去,而且應該連續地,在不同的「剎那」裡存在。所以這個造作之後,就不可避免地,產生一個「時間相」出來。所謂「時間相」,另外一種說法就叫作「遷流」,所以「行」有二個意義:一個叫作「造作」,一個叫作「遷流」。從這個觀點來觀察,實際上造作就是遷流,因為這個遷流原本就造作出來的。
那麼,為什麼要產生這樣的造作呢?如果這個世界,是在一個理性的狀態裡,對大與小不再那麼執著,不再覺得大跟小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情,或覺得大跟小實際上是一件事,只是我們從兩個地方去看它而已,那麼,大的內容裡面,需要小來陪襯。如同走到小人國裡去,覺得人人都很小,那是因為用我們自己的身量和身材跟他們作比較,他們才叫作小;假如我們也化身到小人國裡去,而忘掉我們的過去,這時我們不會覺得小人國的人小,我們會覺得小人國裡,還有我們覺得很大的人在裡面。所以如果在這樣的一種觀照之下的話,我們大小的觀念就不再那麼強烈,開始慢慢地,就消融掉了。然而不幸的是,在一種曚昧的狀態之中,忽然間,我們失掉這種理智的清明,覺得這種東西就是大,大就是很大,大就是好,所以,大就是我要的,小不是我要的。在這樣的處理之下,大與小之間,不知不覺地又作了很大的區分,這樣就開始了「造作」。所以當念頭住於一境(念頭更微細的地方就是住於一境),會凸顯了某一種最深處的一念錯誤,亦即「無明」,使得我們能夠造作,也因為有這樣錯誤的行,其錯誤的識的世界才會顯現出來。
苦的根源
這個形成錯誤的行的無明,不是見思無明,也不是塵沙無明,這樣講的無明是根本無明 │ 最深最細的無明。一片「如的世界」中,嘎然注意到這個「相」,注意再注意,好像顯得它跟其他的相不同,為什麼會突然間注意到這個相的差別呢?就是這個最深層的無明在作祟。
為什麼是根本無明?因為有無明的一動;就是開始有那麼一點從微細到很微細的差別,當注意到它,還沒有仔細地去分別它時,已經是差別了。就這麼一動,無明即現起,差別相立現;也就是說,無明就在那一動的剎那。這一動,並沒有很複雜的念頭,它沒有這個與那個之別,一有差別已經是很粗的無明,即見思無明。現在講的無明,是稍微地注意一下,這一注意造成了錯誤的行;一造成了錯誤的行,即展開了時空。因而可知,在錯誤的行之下,才有幻覺的時空出現;而這個時空,一方面成為我們的幻覺,一方面經由錯誤的行導引,識才有可能產生時間這個東西出來。
無上微妙的深觀緣起
如此從比較深刻的地方來觀察十二緣起的話,這個十二緣起所表現的意義就完全不一樣。這樣子的解釋,不需要三世,從一念的無常之苦,就可以回溯到根本的無明上去;根本無明其實並沒有離我們很遠,所以,不要說根本無明是一個無始無明,雖然我們不懂得什麼叫做無始,可是想像起來卻是很久遠的事情,與近在咫尺的根本無明不太相應。換句話說,在當下的心念之間,不管這一念是愛,還是要取著的心念,或者只是一種感受,在這一念之間,實際上已經俱備了它源頭的無明,因為如果這一念沒有無明的話,這一念的觸、受、愛,就不會造成苦果,它會是一個清淨;但是我們這一念的受、愛、觸並不清淨,因為有執著在裡面,也就是說,這裡面有一個無明的條件存在。在這樣的一種意義下來講,這個深觀的十二緣起,可以是一念之間的十二緣起,不管心念是怎樣一個動法,只要心念一動,就帶著執著,帶著錯覺,那麼這一念之間就含蘊了過去的無明,與未來的生跟老死在裡面。
雖然時間的遷流相,只是我們行的一種造作,使它現出這種遷流的時空出來,但是有時候,在這一分鐘裡,我們從這個受裡,好像因為前面的受,表露出一種愛惡出來,從「時間」上看,就出現了一種因果的關係在裡面。從一念的觀念來講,這一念的受,自相應到這一念的無明,另一念的愛,又自相應到另一念的無明。也就是說,其實這十二緣起本身並沒有時間的次第,在這一剎那,它凸顯出十二緣起的某一支;在下一剎那,又凸顯出十二緣起的另一支。因為這種凸顯,只是它的一種現起,時間的觀念就被消化掉了。這裡最難理解的地方,就是時間是我們在一種無明的狀況之下,給它設立的一種架構。因為這是我們設立的一種架構,好像在這個「迷」的中間,有時間的次第,而這個時間次第實際上也就是一個因果次第。所以,因果的關係,是我們在無明之下所賦予它的一種關係,並不是說有一個「時間」在那個地方,然後我們在時間之流裡,像流水一樣順著流過去;而是整個十二緣起,如果從深觀的角度看,就是一套無明的系統在時間中展現,而變成了我們的生活。所以生活是我們把它放在時間中去展現,並不是它先天俱備了「時間」在裡面。
「時間」與「時間相」的區別不容易理解,但我們可以從電影與影片來想,幫助領會。看電影時,因電影之情節,會覺得有一個時間在流動,可是一卷影片擺在那裡,沒有去放映它的時候,它並沒有時間,沒有人會覺得那個影片有生命。但是如果我們順著這個片子的順序,次第地給它排列出來的時候,忽然感覺到影片裡的東西活起來了,好像有時間了;可是如果不把它放在放映機上演一遍,而是收在箱子裡面的時候,那卷影片上有時間、因果、先後、長度嗎? (只要有時間定有一個長度) 在電影放映的二個小時內,可能電影情節裡的時間是十年、廿年;不管是二個小時還是感覺的十年、廿年,它都有一段時間過去。可是這一段東西當我把它放在一個膠卷盒子裡的時候,從那裡去找個十年?或從那裡去找那二個小時?
不管是深觀或淺觀的十二緣起,要了解,深觀和淺觀並不是兩樣事情。當深觀這個緣起的時候,好像是把一個影片放在這個地方,沒有去放映它,而靜態地、作整體性的結構觀察;淺觀時,就像把這影片放到放映機裡放出來,它就明顯地產生因果次第與時間結構。
從這樣深觀的十二緣起來看,緣起的甚深含義才比較能彰顯。因為緣起的本意,就是「此有故彼有,此無故彼無」,也就是這個世間,過去與現在,原來是互相在緣起,時間在這裡就被化掉了。時間沒有化掉的話,表現成一種不可逆的因果關係;時間一旦化掉的話,這個緣起的世間不是只有這一剎那間的緣起,而是三世的緣起 ─ 過去、現在與末來一同緣起成這樣的世間。
雖然時間化掉了,就某種意義來講,這裡還隱含有時間「相」。這個「相」的存在,可以讓我們有更高的思考層次,去把時間相破除。如此去推論的話,雖然不敢說登峰造極,但卻提顯了一條很遙遠,可以直通「甚深佛意」的道路。因為這種由苦的根柢,找出苦的根據所在,進而把現實裡能夠產生「我執」的根源,一一有順序地倒推回去而導出的十二緣起觀點,才比較能相應到甚深的緣起理論上去。佛當初證悟的十二緣起,如果談的是內證的境界的話,毫無疑問地,是一個很深的緣起,可直接相應到所有高層的佛學裡面去。所以,雖然十二緣起是原始佛教的重要環結,偏屬於小乘的範圍,但是,深觀的十二緣起不是談小乘的十二緣起,而是談直通大乘的十二緣起;這個深觀緣起的理解很重要,因為諸多宗派的緣起理論均以此為基礎。
深觀十二緣起對緣起學說的重要性
我們知道佛法是講緣起的,無論大、小乘或各宗各派,緣起都成為其最中心的學說部份,而十二緣起與每一個學說均絲絲入扣。
業惑緣起
淺觀的十二緣起立場,有一個名稱叫作「業惑緣起」,日本人叫作「業感緣起」。所謂的業惑緣起,就是認為我們這迷惑、痛苦的生命流轉,基本上就是三件事情在流轉:一開始有了無明的迷惑,由於這個迷惑,使得我們作出一些不如理、不合理的行為,行為的結果就是所謂的業;由於我們的惑製造了很多的業,在現實的生活中發生效果出來,就是一個苦的世界。不管是我們的生命,還是所面對的世界,由於一受苦,立刻想要解這種苦,於是就再去造業;這樣子造的結果,又轉生出更多的疑惑。就像吸毒一樣,想要得到樂一點的感筧,所以去吸這個毒品,毒品吸完了之後,讓生理上的腦神經受到破壞,心理上則入到一種恍惚的境界裡去;這樣一來會繼續發展出更多錯誤的了解和感受,這就形成「惑、業、苦」的流轉。
在淺觀的十二緣起裡,把惑、業、苦展現得十分明白,亦即過去的無明 (惑) 造成過去的行 (業) ,然後造成現在的識、名色、六入跟觸、受 (苦) 。受了苦卻不知道苦,所以繼續地造作,於是有了這個愛、取。這個愛實際上又是一種迷惑,有了這個迷惑又去取,這個取則是一個新的業。然後又產生未來的有、生、老死,又是一種苦果,這就是以淺觀的十二緣起來看「惑業苦」的緣起。
這個「惑業苦」緣起,從淺觀的觀點看,還是從一個現象上來看緣起。但是在這樣的緣起裡,為什麼我是我,你是你?為什麼我作的事情要我來受,而不是你來受呢?在淺觀立場上來講,仍然有三世流轉,那麼為什麼這個東西可以從前世帶到這一世,又帶到下一世呢?這些東西,從現象上看,淺觀的十二緣起無法解釋何以這樣的惑、業會帶到今生,再帶到下一世去;或者說,從上一個剎那,帶到下一個剎那。從這個方向繼續去發展,為了要把這些惑、業能夠流轉的基礎找出來,就成了所謂的「阿賴耶緣起」。
阿賴耶緣起
淺觀的十二緣起只有六識: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,前面五識都是我們的感官,很粗淺,不用則無感覺,譬如我們不用眼睛的時候,眼識就停止了,不用耳朵聽的時候,耳識就停止了。因為前五識都會中斷,顯然就不適合作為攜帶業果的基礎,所以在六識裡,可以考慮擔任這個角色的,唯有第六識。
第六識非常地特殊,也非常地靈敏,它通於我們內在的精神,也能夠透過我們前五識的協助,接觸到外在的境界。但是,這樣一個第六意識,能不能作為基礎呢?還是不能,因為第六意識也會突然停止,譬如有人突然昏過去了,過了兩三個小時,他還不知道已經過了兩三個小時,換句話說,在這段昏厥的時間,第六意識是停止的狀態。可見得,第六意識並不是連續的東西,它在時間之流中,也是會中斷的,所以也不能擔負攜帶業果的責任。在小乘佛學裡,因為只談六識,所以在討論這個問題時,就想辦法創造其它的角色出來,譬如有些人就製造出「我」的觀念,另一些人就製造出一種叫作細意識的,就是說,勉強地在第六意識後面,認可一個很微細的,平常沒有感覺到的東西。這樣的觀念,後來慢慢地發展,就成了大乘裡法相唯識宗的「八識」的觀念。
「八識」就是除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識之外,加上第七識,名為「末那」,又加上第八識,叫作「阿賴耶」︵簡稱賴耶︶。雖然分成八識,其實它的重心是在第七、八識上,因為六識中,沒有一個可以作為因果或業果傳遞的主體,必須是在六識之下,還有一個更深刻的識。這個識雖然還是「識」,可是它的分別力非常地微細,前六識沒有辦法感覺到它的存在。這個識不像前六識一樣會間斷,雖然它的作用非常地微細,可是它卻是不間斷的。這裡面當然牽涉了一大套的學問,譬如說所謂的「不間斷」,是「不斷不常」,不是我們想像的永恆,但是它又不會間斷,那它是什麼呢?這就有如流水和瀑布,長水大河好像是一個連續的東西,但是仔細看看,它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個流動的東西,換句話說,這流水的每一點都是新的一點,而新新不已。所以從新新不已的觀點來講,它是無常的,因為它沒有真正的不變過,它永遠在變;但是從相續的觀念來講,可以說它是不斷的,「抽刀斷水水更流」,沒有辦法把水切斷旳。藉此譬喻,可以瞭解七、八識也像這個流水或瀑布一樣,沒有間斷,但也不是恆長。
七、八識概略說起來是一體的,但為了要解釋意識之中的我執,所以建立了第七識。譬如說我們平常有一種我執,感覺有一個我的概念在其中,這個是第六識裡的我執;可是當深度的睡眠或是昏倒,第六識不現形的時候,我執是不是就斷掉了呢?如果我執可以斷一個鐘頭,應該我們就可以解脫了,也許不要斷一個鐘頭,說不定一分鐘,我們就解脫了,就開悟了,但是我們沒有開悟,沒有解脫,這表示我們的第六意識中斷的時候,還有一些微的我執在那裡,持續不間斷地產生一種執著。
第七識跟第六識的我執不一樣,第六識的我執是很粗顯的,但是會間斷;第七識的我執是不明顯的,非常潛在的,有時候我們說,修行了大半輩子,怎麼忽然就發脾氣了?雖然很清楚不應該發這個脾氣,可是這個脾氣發得沒有來由,而且發得很強烈,所以必然有比我們第六識更深細的一種分別或執著在裏面。這就是第七識的功能,它不斷地在那裡執著一個我,執著什麼東西是我呢?它執著的就是阿賴耶,嚴格地講,它執著的是阿賴耶裡的一個見分,但大略地講,就是因為這個阿賴耶在某種意義上有一個不斷的性格,維持了某種恆長性,像我們的流水一樣。
由於有這樣的相續性,阿賴耶識才有這種不斷不常的恆長性在裡面,因此第七識可以把第八識想像成是一個「我」,這是第七識的一個功能。這樣的解釋,的確在世界的發生和現起,以及知識方面的過程,都比小乘的淺觀十二緣起精確,而與深觀的理論相應。若更細一點分析,第七識對阿賴耶見分的執著,本身就是一個十二緣起的現起;雖然已經是如此地細了,在第七與第八識內的見、相二分的剎那,以及在第七識執著第八識見分的剎那,十二緣起的每一支,支支分明。(寫到這裏,忽爾嚎啕大哭,感歎佛陀所證悟十二緣起的深邃,對佛慈悲示現的恩典,無以回報,真是汗顏報憾,淚流滿龐。是為記。 )
對「賴耶源起」有了這樣「深觀的十二緣起」的理解,其實已經進入「真如緣起」,甚至很直接地相應到華嚴境界的「法界緣起」或「無盡緣起」,乃至於天台的「一念緣起」。這就是為什麼十二緣起應該有深觀的一面,因為深觀的十二緣起直接相應到「法界緣起」跟「一念緣起」,這樣子我們才可以說十二緣起甚深。
修行的緣起觀
不論淺觀或深觀,說十二緣起的目的,都是為了要說明為什麼我們當下的存在要這樣子存在,為什麼我們會這麼苦,以及苦的生命是怎樣子形成的。我們已經理解到這樣的一種存在是苦的存在,我們也看出了苦原來是這樣子緣起而出現的。不管從深觀或淺觀的角度,我們都得到了一個不同但很具體的概念,在深觀上我們了解,在這一套緣起裡,此有故彼有,所以一旦有了一個,其它就全部都有了;在淺觀裡,我們瞭解時間是因果的鎖鏈,在這個鎖鏈之中,如果俱備了前緣,就逃不掉後面的結果,因為它有個限制性在裡面。
生命的流轉
我們的生命,如果從淺觀的立場上講,是被束縛住了,因為不管從二世還是三世來看,過去已經有了「無明」和「行」,這件事已經是個無可更改的事實,我們又不幸入胎生下來了,俱備了這樣一個身體,從這個身體上我們又很自然地產生了「觸」,又得到了受,而對這個受產生了一種執著,從這個受的執著裡,又發生了「愛惡」,因為愛惡的關係,有些是我們喜歡的,有些是我們討厭的,於是就爭取或排斥,所以這時我們又產生了「取」。這個生命,一旦流轉,就會如此無可奈何地,輾轉產生今生的生、老死,或來生的生、老死,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。所以觀察這樣一個現象,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:生命如果不作任何努力的話,順著這個十二緣起流轉下去,將是一個無盡無止的流轉,而沒有任何的出路,這個現象,我們在佛學裡面就叫作「流轉門」。
解脫的還滅
生命既然是以這樣的因緣與次第在無盡地流轉,那我們有沒有希望可以從這個流轉裡頭解脫出來?這是我們學佛真正的問題所在,其中心的目標,就是希望能透過這個流轉的解析,找到一個解脫的方法。這解脫的關鍵或法門,將使得我們這痛苦流轉的生命可以停止下來,得到一種休息,這條路就叫作「還滅門」。
流轉與還滅
研究生命與解脫,要同時從這兩個角度,一方面看流轉,再方面看還滅;也就是說,瞭解了生命的流轉之後,要從這樣的流轉裡,找出還滅的契機在何處,這就是修行人要把握的中心。
小乘的修行:從淺觀的觀點來說,因為有時間的先後與三世的因果,緣起雖然也有無明作為它的基礎,但卻是過去生的無明。我們不能像走時光隧道一樣,回到過去生,再去修正過去的「無明」跟「行」,同時也無法變動父母給我們身體的「識」、「名色」與「六入」。再者,因為未來我們無從接觸,未來的生跟老死,那是未來世的事情,也是我們想要把它解脫的事情,所以也不是我們能夠著力的地方。因此如果把十二緣起,連頭帶尾地,丟掉這些無能為力的支,我們還剩下什麼呢?只有「觸」、「受」、「愛」、「取」、「有」。
在這五支裡,雖是我們現在生的,但「有」是「取」的一個結果,因為有了這個取造成了這些事情,它已經留下了一些因子,使得產生未來的苦果,儘管這個苦果一時之間還沒有現起,但是這個根已經種下去了 │ 沒辦法把已經得到的根,再把它重根挖掉。所以這裡面,真正讓我們感到還可以處理的,只剩下「觸」、「受」、「愛」三支,可是在觸的地方時間很短促,因為在一觸之下,我們也已經不能再回頭了,也不能防止繼續地再生觸,所以「觸」這一支也不太能夠著力,如此一來,最後只剩下「受」跟「愛」這兩支。
「愛」與「受」成為我們今生需要著力的地方,但是這個「受」裡所產生的苦、樂感覺,卻是受了我們過去的習氣與因緣而現起,往往也是很不由自主地,所以在這僅剩的兩支裡,第一個我們要把握的,就是愛這一支。當我們有了苦、樂的感受,或如意、不如意的感覺,在要產生慾望的時候,可以稍微留意,再等一下;這裡是十二緣起中,唯一還有時間讓我們再等一下的一支。「等一下」的意思是說,根據十二緣起旳道理,假如現在有了受,但不因這個受而產生慾望去追求,或者去排斥,那麼就不會因為這個受帶來一些更多、更複雜的行為出來。這樣子的話,在往後的緣起上,就不會再有新的結果出來;所以在這個意義下,雖然我們不能夠把緣起斷掉,但是至少我們已經可以控制這個緣起。
這樣子的思維,就產生了小乘修行的哲學,以斷愛慾為主,換句話說,根據十二緣起的反省,只有在受跟愛這個地方可以著力,而比較容易而有時間著力的地方,就是愛這支,因此要用種種的道理和戒律方式,使之了解,不要去順從自己的慾望,要把慾望降到很低,甚至於沒有的程度,這樣子就可以在某種意義下使十二緣起的鍊子切斷。如果我們真的把愛斷乾淨,則不是在斷一種慾望,而是在斷所有的慾望,那麼結果就不一樣了,因為在斷盡所有的慾望之後,任何的取都沒有辦法發生,這時候因緣的鎖鍊就斷掉,這個在小乘佛法裡,就是得到了解脫 │ 一種究竟的解脫。
斷愛慾更好的方法是,更進一步去控制受,使在受的地方得到一種平和的受,在修行的層次上,若到了這麼一個狀態,就是任何的受不會變成一種強烈的感受,這樣子就根本連愛的機會都沒有了,所以更徹底一點。這樣的看法,在小乘裡就是他們「還滅門」的看法 │ 如何斷掉愛慾。
大乘的修行:從深觀的觀念來講,這個十二緣起「一有一切有」;同樣地,依照深觀緣起的觀點,也可以「一無一切無」。既然老、死跟著「無明」、「行」纏結在一塊兒,如果在這個十二緣起裡,能夠在一念之間把緣起的條件變動,庶幾乎我們可以跟「十二緣起」不緣起,也就是「一滅一切滅」。在這樣的深觀看法裡面,整個十二緣起是在「無明」下面,因為我們了解到,這整個的根,是有一個錯誤的「無明」在這個地方;我們又了解,我們的念念都俱備十二緣起,所以我們念念之間都有無明。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在這一念之間把握得好,使這個無明不起,至少我們是一念的解脫,假如我們能夠念念的無明都不現起,那就是念念的解脫。這就是阿彌陀經所說的「一心不亂」與「心不顛倒」的真諦,也是禪宗行者參話頭的用意。
緣起觀的「理」與修行的「事」
不論小乘或大乘,深觀或淺觀,在對緣起的「理」了解以後,我們已經找到一個修行的方向了,照理說,可以開始修行了,但是我們還需要多了解一下。雖然在理路上我們有了一個脈絡,但是「理」跟「事」都要能照顧到,才不會執事廢理,或執理廢事,因為這個世間是一個「理」跟「事」都存在的世界,所以如果只看理這一邊的話,有時候會陷入一個迷惑裡去,所以我們在看過「理」後,要回過頭來看看這個「事」的世界是怎樣的世界。就是說,我們講三世,也講輪迴;但是輪迴並不是每個人都清楚,在學佛上,它跟我們的修行又有很深的關聯和意義。從覺悟的觀點講,本來我們也是應該要多了解一些宇宙裡面種種的現象,因此對「宇宙有情狀況」和「宇宙器界概說」,就不能不下點功夫去研究。能夠如此把握,學佛的道路,才算真正地確定。